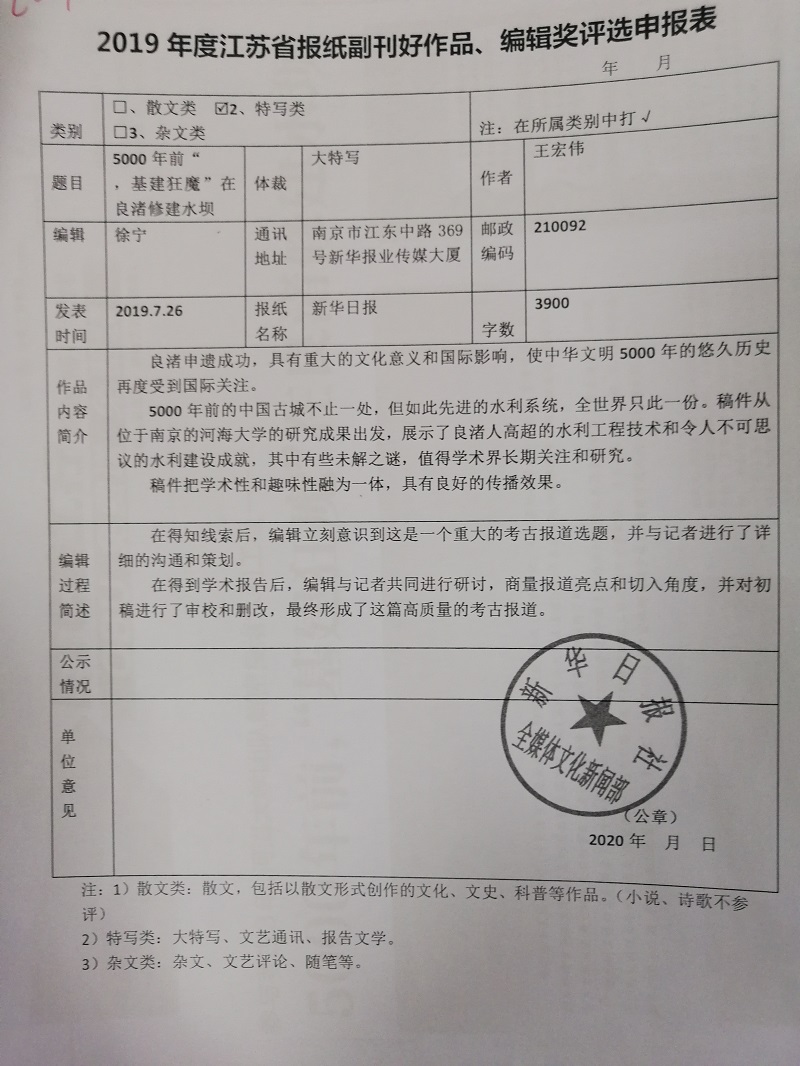
参与考古3年,河海大学团队解密良渚水利工程 ——
5000年前,“基建狂魔”在良渚修建水坝
“他们义务完成的工作,对良渚申遗是关键时刻的雪中送炭,是救了我们一把。”浙江省文物考古所研究员、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考古领队王宁远7月15日在朋友圈发了一篇《写给河海大学良渚团队》,让良渚古城外围水利考古的幕后英雄、河海大学岩土力学与堤坝工程重点实验室在良渚古城成功申遗中的贡献被公众所了解。
他们的工作向世界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事实:早在5000年前,中国良渚的水利工程技术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王宁远说:“网友调侃当今的中国是‘基建狂魔’,因为中国正在不断建设超级工程并刷新世界纪录。其实早在5000年前,比大禹治水还要早1000年左右,中华大地上就有一群‘基建狂魔’,他们不但修建了宏伟的良渚古城,还修建了庞大的古城外围水利系统。”
▋超级工程,改写中国和世界水利史
外围水利系统被列为良渚古城申遗的重要内容,包括谷口高坝、平原低坝、塘山长堤共11条水坝,它们控制和影响的流域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不仅把中国水坝的历史往前推进了1000多年,也改写了世界水利史。
这完全超出了学术界的预期,即使这套水利在30多年间被逐步了解和考古发掘之后,在2016年3月的研讨会上,国内顶级水利专家仍然不敢相信,5000年前良渚先民竟然在几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规划、建设了一个如此庞大的水坝群。它们可以为古城防洪吗?溢洪道在哪里?蓄水、排水和调控如何实现?会不会是城墙或地基?会不会是抵挡海潮的堤防……太多的疑问等待科学研究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
河海团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参与了良渚水利系统与工程技术研究。2016年11月,河海团队来到现场。“站在小山包上面对山谷张开双臂,右臂指向岗公岭水坝,左臂指向老虎岭水坝,两道坝在山两侧拉出一条笔直的线,想象着5000年前的水库,可以充分感受到我们祖先的聪明才智。”河海团队外援、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赵晓豹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从那一天起,河海团队在3年里走遍了与水坝相关的每一座山,调研了周边1000多平方公里的水文与地质情况,逐渐破解了良渚水利工程之谜。
展开示意图,河海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教授袁俊平告诉记者,良渚古城处于一个C形区域中,三面环山,只有东面朝向杭嘉湖平原,加之水网密布,既安全又适宜稻作生产。出于对水资源的管理,良渚先民们在三个区域修筑了11条水坝,整个水利系统在良渚古城北部和西北部形成面积约13平方公里的储水面,其中古城西北方的群山中有6条水坝分为东西两组,它们位于谷口控扼两条水道,因所处位置较高被称为“谷口高坝”。其中东高坝(岗公岭、老虎岭和周家畈)拦蓄出库容为1310万立方米的水库,西高坝(秋坞、石坞和蜜蜂垄)拦蓄出库容为34万立方米的水库;古城西侧三四公里外的平原弧丘间,有4条水坝(狮子山、鲤鱼山、官山和梧桐弄),因所处位置较低被称为“平原低坝”;古城北侧大遮山脚下有两条平行的东西向长坝,现存长度达5公里,是水利系统中体量最大的,被称为“塘山长堤”。平原低坝和塘山长堤形成的水库容量达3290万立方米。
经过精确测算,所有坝体的土方量总计为288万立方米,按每立方米土的开挖、运输、填筑需要3个人工计算,建筑全部11条坝体大约需要860万个人工;若由1万人来建造,大约需要连续不断工作两年半,如果以每年农闲时间有100天参与建设,1万人完成水利系统建造需要近9年,综合考虑古城和水利系统建设(良渚古城及水利系统工程量总计约1005万立方米),则需要几十年时间。在5000年前,只有一个强盛的国家,才能进行这么复杂的规划设计,才能调动这么多的人力、物力持续进行工程建设,并完成后勤保障。
河海团队的研究为良渚古城申遗提供了坚实的学术基础,他们的学术成果被作为申遗文本附件提交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距离遗产评估专家到现场考察不足一个月时,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忽然来函要求提供关于良渚水利系统和中国古代水利工程方面的专门资讯,河海团队临危受命,为ICOMOS专家做了两场水利系统研究专题汇报,并在河海大学土木与交通学院和浙江省考古所联合建立的实验室中进行了筑坝技术原理演示。听完汇报,考察专家丽玛胡贾女士说:“我没有任何问题了。”
▋不可思议,规划之精密刷新专家认知
“说到大坝,人们往往想到防洪,但防洪并不是良渚人修建水坝的唯一原因,甚至可能不是主要原因,否则他们搬家就好了,那比筑坝更省事。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更可能是为了服务古城的生产生活而修建的系统工程。”赵晓豹说,“我们总觉得5000年前人类的技术还很原始,但这套水利设施的规划设计和建造工艺刷新了我们的认知。”
碳14测年显示,水利系统与古良渚城内重要建筑的建设时间是基本一致的,也就是说,二者是被通盘考虑、统一规划的。那里所在的天目山系是浙江省最大的暴雨中心,每到雨季常常山洪泛滥,溪满成灾,直到今天该地区的西险大塘还是杭州市抗洪除险的重点区域。研究发现若缺少外围水利系统,来自北方大遮山和西北山谷的洪水将对古城及附近遗址带来较大的冲击,尤其是大遮山下的塘山长堤中段,对古城防洪具有重要作用。
同时,蓄水也是水坝的基本功能。良渚人筑坝时,通常在坝体内填筑淤泥和草裹淤泥,坝体外侧用黄色黏土作为坝壳。这一结构类似于现代的粘土心墙坝,心墙起防渗作用,而坝壳则起到保护和支持坝体稳定的作用。取样试验表明,这种坝体的渗透系数大约为10-5-10-7cm/s,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因为它达到了现代工程中防渗材料的要求。
这些水坝也形成了完整的航运通道。水利系统建成后,形成了上下游两级水库,其中下游水库的水面正好抵达上游高坝的坡脚,配合原有河道和水域,就形成了从古城到下游库区再到高坝以北3公里远的运输通道。良渚人没有发明轮子,古城四周的水城门多达8个,而陆城门只有1个,佐证了当时的交通运输主要依赖竹筏和独木舟进行水运。当时运输的物资主要有木料、石料和玉料等,在莫角山宫殿区东侧的河道中发现了3根18米长的大木料,另外古城的河道采用了大量木料护坡,这些木材应该是从山里采伐后运来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想像古城内外舟楫往来的繁忙景象。
“我们认为良渚水利系统还有灌溉功能,因为下游水库的鲤鱼山、前村畈、横堂山等处坝下的土层中发现了高密度的水稻植硅体,这意味着上述地区在当时很可能存在稻田,而它们都处于低坝库区的下游,可以通过引水实现自流灌溉。”袁俊平说,“此外,良渚水利系统还应该具有调节水系的功能,古城位于低坝库区的东侧,城内的生活、手工业制作、城内外的农业灌溉和航运,都需要稳定的供水。”
了解水利的人都知道,修筑土坝时一定要留出溢洪道,当洪水过大时可从溢洪道泄流,以免水位上涨从坝顶溢流造成溃坝。在良渚水利工程中,先民们利用了天然山谷作为溢洪道泄洪。以东高坝为例,三条水坝的坝顶为海拔30米,在水库东侧发现一个海拔28.9米的山谷隘口。水力计算表明,当隘口水位为30米时,隘口的泄洪能力大于计算出的最大洪峰流量,完全可以保障水坝安全无虞。如果坝体低于隘口会造成坝顶溢流溃坝,坝体过高则会浪费人力、物力,而目前的坝高最为科学、恰当,这表明良渚先民有高超的水利规划能力。
▋未解之谜,良渚人从哪里获得“上帝视角”
早在良渚先民出现在这片土地上之前,崧泽文化(距今6000年至5300年之间)就在这里留下了遗迹,考古发现表明,崧泽先民无力改造自然,只能住在高地上。
然而良渚人则完全不同。碳14测年表明,良渚古城和水坝的始建时间均在5000多年前的良渚文化早期,其中水坝建设持续了四五百年之久,也就是说良渚先民刚在这里站稳脚跟,就开始雄心勃勃地要改天换地,单单兴建莫角山宫殿区,他们就把地面垫高了大约15米。
良渚水利系统总土方量约为288万立方米,蓄水总量则达到4600万立方米,工程量与蓄水量的比例约为1:16,即使以现代水利工程标准来衡量,良渚水利系统也是非常高效的。最远的坝体与古城间的直线距离约11千米;高坝与低坝间距离达3.5千米;塘山长堤距离古城最近,约在城北2千米处,整个工程超出了肉眼所能看到的距离。今天我们有GPS,有遥感和测绘技术,还有卫星图片,而良渚人从哪里获得了“上帝视角”,使他们可以在数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规划设计如此庞大和高效的水利工程?
坝体的高度同样被控制得相当精确。东高坝三条坝的坝顶均为海拔30米,西高坝三条坝的坝顶均为海拔40米,平原低坝坝顶均为海拔10米,它们之间被山体隔断,那么良渚人又用什么办法来控制坝体的高程?
在修筑水坝的过程中,良渚先民大量使用一种被称为草裹泥的工艺。先民们在沼泽地上取土,然后用茅荻包裹土块,再用竹篾进行绑扎固定,最终以纵横交错的方式进行堆筑。实验表明,通过草裹可以提高泥土的强度达6倍,而纵横交错堆砌的承载力是顺缝摆放的2倍,这种工艺相当于现代抗洪抢险时的沙包或土工袋,可见良渚人对于水利工程施工已经有了相当深刻的了解。
直到良渚文明衰落时,水利系统仍然在正常发挥功能。王宁远告诉记者,良渚文明为何在距今约4300年前突然衰落,学术界有不同观点,其中一种认为原因是当时发生了大洪水。研究表明,在嘉兴、德清、良渚地区的广大区域里,地层中都发现了一种黄粉土,它们来自长江入海口,被海潮带到杭州湾,再被冲到今天浙江杭嘉湖地区。混合着海水的洪水使良渚地区变成了一片盐碱滩涂,更可怕的是这样的大洪水反复发生,在良渚古城的低洼处形成了一两米厚的黄粉土堆积,良渚人的家园就这样被彻底摧毁了。良渚人撤退了,这些水坝却留了下来,直到2000年后的商代,人们为了排水在蜜蜂垄上挖掘了沟槽,直到5000年后的今天,石坞拦出的湖边人们开起了农家乐,塘山长堤的北侧仍然有被水坝拦蓄成的长庆湖。
这11条水坝,是良渚人的伟大创造,也是5000年前世界上最发达的水利系统。那么,良渚先民们究竟用什么方法进行测绘和计算?他们这种成熟的规划、设计和施工能力又从何而来?中华文明的创造密码和原始基因也许就蕴藏在这些水坝中。
本报记者 王宏伟 本报实习生 王 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