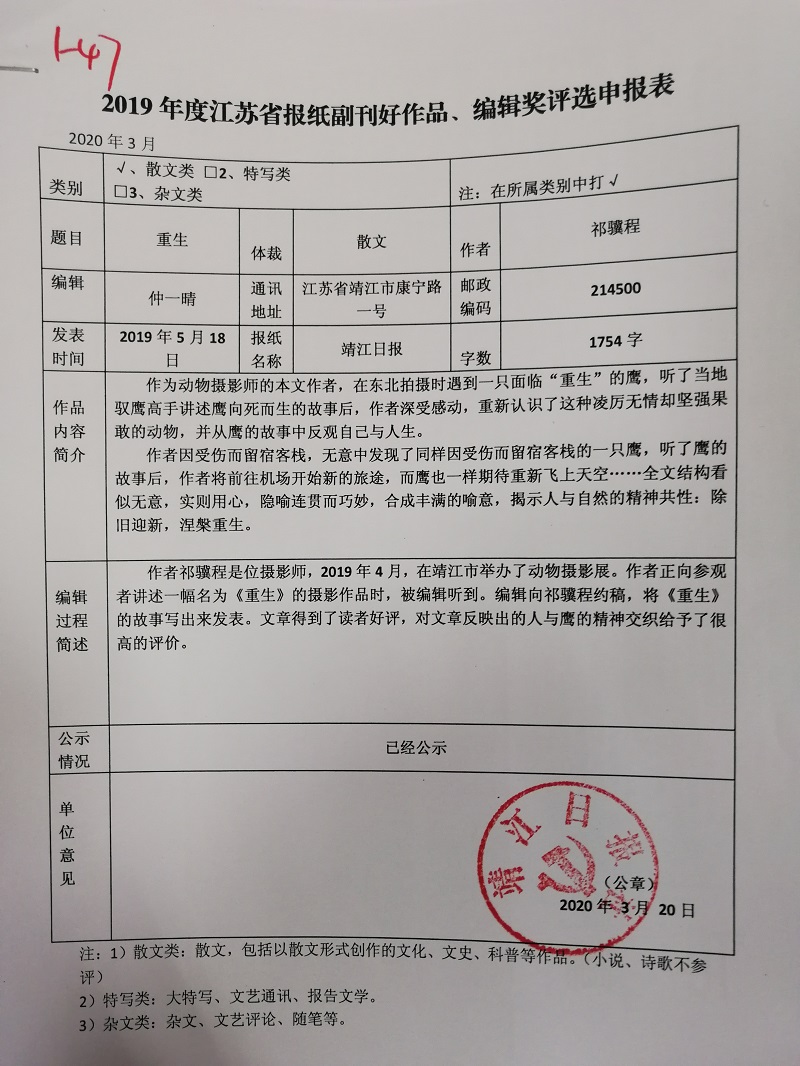
重 生
祁骥程
说实话,原先我并不喜欢鹰,因为,我不习惯仰视,更不喜欢它俯冲时带来的死亡气息和盛气凌人的压迫感。
直到有一天,我遇到了一只鹰,并听到了关于它的故事……
2017年隆冬,为了完善我的鸟类拍摄,我背着沉重的行囊,独自深入吉林旷寂的雪原拍鹰。连续三天起早摸黑,在寒冷的雪窝里蹲守,眼睛被白茫茫的原野刺得红肿,零下三十五度的寒流几乎将我的眼睛、眉毛和嘴唇冻黏在一起,拍摄中不得已裸露的手指被冻伤,甚至无法驾驭碗筷,脚后跟裂开的数道口子,每走一步都针扎般的疼。无奈之下决定休整一天。
住宿的客栈位于吉林山区一个偏远的满族乡寨,叫鹰屯,隶属打渔楼村。那天早晨,我一直待在暖暖的炕上直到炭火熄灭才恋恋不舍地起床。清晨的阳光将窗户上的雾珠染成了一片晶莹的橘色,温暖而明媚,让我忘却了一窗之隔的冰天雪地。早餐后想到院中溜达一圈,推开厚厚的大门,一口寒凉的空气似冰泉般呛入肺腑,如食芥末,吓得我赶紧拢上大衣竖起毛领,将自己裹得密不透风。客栈大院里一排刷着“猛禽救助站”大字的土屋子引起了我的好奇,屋子应该是用泥巴和麦秸秆搭成。四下无人可询,我便径直走过去想一探究竟。
推开门的刹那,一声惊觉而嘶哑的叫声从昏暗处传来,令人毛骨悚然!我瞪大双眼急速地在黑暗中搜寻声音的来源,半晌,才发现声音发自地上,一只瘦骨嶙峋的巨鹰站在地桩上,恐怖而怪异。它很瘦,一只鹰目戴着眼罩,翅膀松软地挂在肩上,灰黑色的羽毛稀疏而凌乱,腿和脚趾都缠着绷带,仅露的一只眼透着灼灼光芒,在黑暗里闪烁。待惊恐稍稍平复后,我方敢小心翼翼推开里间的一扇房门,布帘遮着的小屋,光线柔和而明亮,屋里弥漫着浓烈的烟酒味,“大兄弟,吓着了吧,进来炕上坐。”我循声向屋里望去,在炕上斜倚着一个戴着狐皮帽矮小的中年人,正眯着眼悠闲地吸着旱烟,哈,原来是他!天天在一个锅里吃饭,是客栈的后勤,一个满族汉子,别看他个头矮小,却是骑马驭鹰的高手。
他看我满脸的狐疑就接着说:“这只鹰是一个星期前附近山民送来的,被发现时已经奄奄一息了。一只翅膀骨折,一只眼睛有严重眼疾,三个脚趾腐烂发炎,现在上药绑扎好了,将它关在黑屋子里是让它好好休息,明年春天仍会将它放归山林,但是它能不能活就看造化了。”
“啊,放回山林不是治愈了吗?怎么还要看运气呢?”我是越发不懂了。
“现在是冬天,天气太冷,加上食物短缺和体能下降,若不救治肯定会死。但明年它回归山林仍要渡过难关。”满族汉子看我愣愣站着继续讲述着,“猛禽的寿命通常有二十到七十年,不同品种有很大差异。但并非每只鹰都能活到这个岁数,当鹰活到三十多岁时,它的身体开始发生变化,长年穿梭于风雨雷电和深山丛林中,身上会留有多处伤口,羽毛也会破损褪化,最主要的是它的喙和爪也开始钝化变老,无法有效捕捉猎物。这时的鹰将面临着生死抉择:要么一天天消瘦等死,要么脱胎换骨,重生!”
我屏住呼吸急切地问道:“它如何重生?”
“我也没看见过,但坊间传闻它们会选择幼小动物,先填饱肚子,然后觅一处高山崖壁筑巢,减少外来侵入。在接下来的六个月内,它先用喙击打岩石并使之脱落,待新的喙长出后,它再用喙将老化的指甲一一拔去,直到指甲重新长出来,最后它会将身上破损和老化的飞羽拔光,待新的羽毛丰满后,便换来四十年的寿命。”满族汉子操着纯正的东北话声情并茂地讲述着,“我不确定这只大鹰遭遇了什么,但根据它的年龄和伤势来判断,正如传说中的,它正在经历重生过程,只是恰逢冬季,它熬不过去,先养好伤待明年春天回归自然后,它仍需进行这个过程,谁也帮不了它。”
屋里静了下来,他没有再讲,我也没有再问。
生命是如此脆弱,万物轮回谁也无法抗拒;生命又是如此坚强,草可以春风又绿,鹰可以浴血重生。而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一边被光阴滋养着慵懒懈怠,一边被岁月侵蚀着日渐年迈,等死?重生?我们和鹰一样面临着抉择。吴冠中先生说过:“时代一定会有真诚的挽留和无情的淘汰……真正的艺术家是供养不出来的,要让生活来养他,让社会来养他,让苦难来养他。”
离开鹰屯的那天早晨,司机早早来到客栈的院内等候接我去机场,行装收拾完毕后,我没有直接上车,而是再次推开了那扇土屋的大门,最后再看它一眼……
车在飞驰,辽阔的雪原在缓缓向后移动,抬头远望,逶迤的山岗上雄鹰正展翅飞翔,它是自己的英雄,它铁一般的翅膀担得起漫天风雪,也担得起任何仰望的目光,蓦然间我的眼里噙满泪水。
谢谢这片土地!
谢谢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