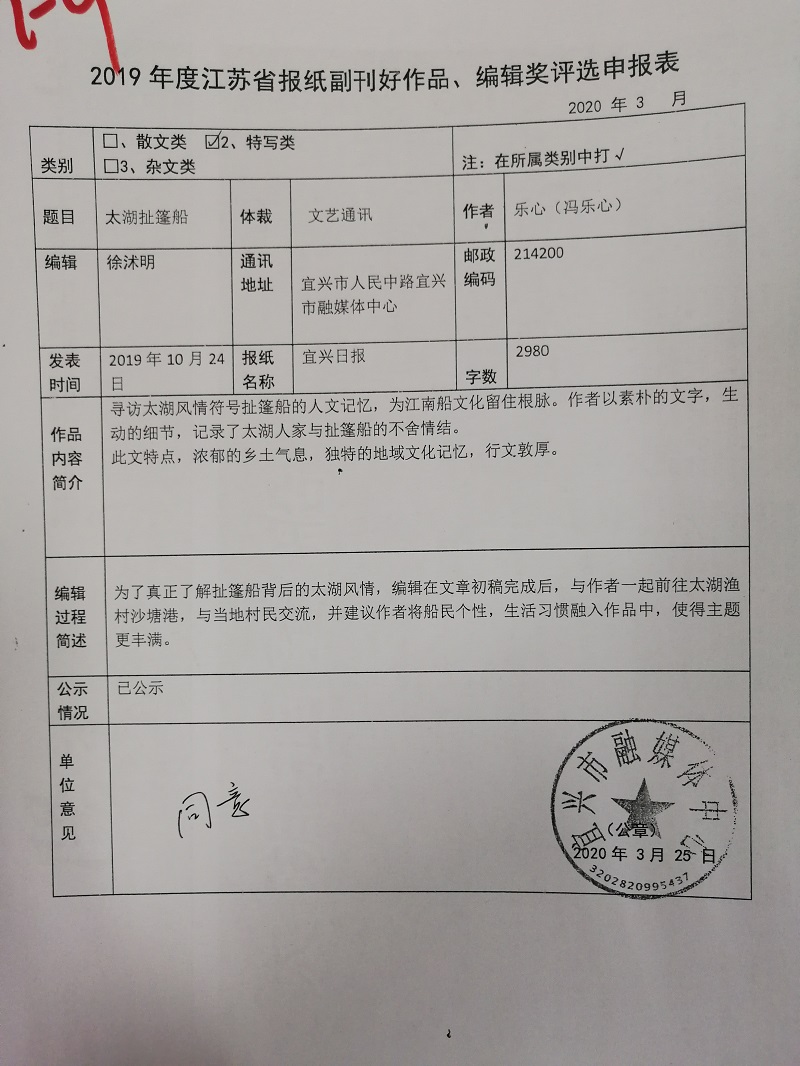
太湖扯篷船
乐 心
引言
太湖九月开捕,渔港里歇了几百只铁驳船,渔民在船上挂了几面红旗。一早铁驳船开足马力驶向太湖,船上的红旗迎风猎猎作响,这很容易让人想起过去扬帆航行的扯篷船。在过去的年代里,扯篷船是太湖人家的生活船、生命船,上世纪70年代还能见到扯篷船,现今已从他们的生活中消逝了。我在太湖边寻访到三位长者,录下太湖风情符号扯篷船的难忘记忆。
(一)
一出沙塘港,就是太湖,浩瀚的太湖,一望无际。
杭家父女驾扯篷船到无锡卖菜。这天湖面上刮东南风,船驶入太湖不久,桅杆上扯起了二道篷帆。父亲在头篷,根据风力放篷脚,以篷脚的宽紧来掌握船的速度,女儿在后艄掌舵管船行进方向,根据风向调戗。
船到马山附近,风向由南转东北,变为逆风,必须调戗。另一同向的船先调戗,暗樯戗往右,杭家父女的船为开樯戗,父亲此时在船头点烟没注意,两船行将相撞。女儿呼,爹爹,快,我要调戗了,父亲扔掉了香烟立即在前面配合收紧篷脚。瞬间,两船避开,好险,差点就要撞上。相邻的船家见到这一幕,称赞不已,这丫头厉害,小小年纪就会驾船了。这一年杭令郎9岁。
杭令郎父母生养了11个儿女,4个儿子没养大先后夭折,家中清一色7个女儿,父亲把三丫头令郎当男儿养,六岁就带她上船,大人上岸卖菜,她看船。八岁她就会帮衬着开船,跟父亲在风口浪尖上讨生活。太湖时常风急浪高,波涛汹涌,摔打出了一批批太湖之乡的气魄男儿,而杭令郎从小像男儿一样在风浪中搏击,养成了胆大心细的性格。过去太湖五六级风浪的时候,一般船不敢航行了,杭令郎驾着船总能安全返回,村里人都讲,癞团荣彪的三丫头厉害!令郎的父亲杭荣彪模样胖,村里人叫他癞团荣彪,癞团是蛤蟆的俗称。
杭令郎胆大心细,在茫茫太湖中扯起篷帆,全凭丰富的航船经验。有时候从无锡卖菜回来已是天暗,黑暗中航行,她以前方的灯光,天上星星,月亮,山影为固定点,定目标,或者看浪花风向定目标,还有用篙触湖底硬度,是硬底还是软底可以判断船在什么位置。她这辈子最傲健的一次,驾船到无锡卖菜,一担两大筐挑了206斤大蒜,从无锡西门码头挑到崇安寺。买卖双方交易过秤,买方不信,你一个女娘家怎会挑得动206斤,肯定称错了。重称,确实是这样,没称错。
村上老一辈的男人至今都佩服她,不光驾船是高手,针线活也出挑,从摇棉花、染线、到梏机上织布,做鞋子,做衣裳样样都会,家中六个儿女小时候的衣服都是她缝制。我见到杭令郎的那一年,她84岁,满头白发,身板硬朗。她用一只细黑夹子将右边的白发别住,露出了宽大的额头,既清爽又精神,笑起来像经岁月风霜的一丛菊。当时,她是沙塘港里最后一位精通扯篷船驾驶的女子。
(二)
村庄,一大片灰色老屋,有一间老屋传出木刨声、凿子声和讲话声。
廖木匠在推刨,郑木匠在打槽,许木匠坐长凳上抽烟。
这间老屋是郑木匠的工场,其他两位老师傅其实早已不做木匠活了,但一有空他们就来坐坐,讲讲经,搭把手过把木匠瘾。
郑木匠大名郑顺华,讲话中气足,一开口就好像装了个高音喇叭似的,老远就听到他声音。他手里拿的竹笔,也叫画字,传统工匠用来画线的工具。竹笔画出来的线,一是直二是细,细到头发丝一样。竹笔比铅笔和水笔画出来的线更精确。只见他画好线,凿物件时将凿子放边上的油缸里醮醮。这只油缸他已用了几十年,木头做的,里面放豆油和棉花。靠墙的板壁上插着二十多把凿子,斜凿、方凿、圆凿,尺寸从三厘米到三毫米不等。长条案板上摆放着各种刨子:线刨、剜刨、槽刨、小方刨、二四线刨、特块刨、小圆刨、短光刨、速腰刨、洋线刨、圆刨、边刨、一字刨、长刨、泵刨、沟刨等等。老木匠讲,做到做不动的时候,将工具收起来装箱,留给后代作个纪念。
这样的老木匠已不多见了,有人请他出山打造古典建筑,做传统家具,老木匠兴趣不大,他在家里痴迷打船。他对船的感情来自于父辈,打小他就听父亲讲述风口浪尖的航行生活,讲太湖船神赤脚黄泥郎的故事。
黄泥郎是沙塘港附近的一名年轻后生,乐于助人且水性好、有高超的驾船技术。只要太湖有船遇难,他鞋子都来不及穿,赤着脚奔去救难,所以称他为赤脚黄泥郎。相传,西汉光武帝刘秀在太湖遇险,黄泥郎挺身救护使他转危为安。刘秀登基后感念救护之恩封他为“黄泥相公”。黄泥郎在一次施救中遇难,后人为纪念他,在太湖边建“黄泥相公庵”,为他塑像,敬奉为“船神”。
郑木匠正是听着黄泥郎的故事长大,他17岁时跟修船的父亲学木工手艺,几十年下来,锯、刨、凿、雕,无不精通。现如今航船逐渐退出了日常生活,扯篷船已成遥远的记忆,郑顺华对船的情结却日益加深,他想亲手打造一艘扯篷船,让后人感知太湖船文化。郑木匠日夜构思,设计船样,修改船头船艄的尺寸,花八个月时间全手工打造了一艘四米长的三桅扯篷船。虽然是微型压缩版的扯篷船,但非常逼真,船上篷、樯、篙、舵、橇、铁锚、铁索齐全。船舱门上雕刻的仙鹤,细部见刀工精致。这是他的呕心沥血之作,整艘船弧形拼装,榫卯对接,制作精巧,无不显示他高超的技艺。村上驾过船的老人都来看,亲手摸摸,熟稔得像回到了从前。
(三)
胡岳良和郑顺华有亲戚关系,两人年纪差不多大,彼此讲得来。老胡有文化,这几年他收集整理了不少太湖船文化的资料,他们碰到一起就聊太湖航船经。两人利用村里的闲置房搞了个太湖船文化展览室,郑木匠将自己打造的三桅扯篷船贡献出来,老胡负责展览室的图文内容布置。
老胡讲,扯篷船对我们和我们的前辈来说太重要了,那时候太湖终年舟船往来,风帆点点,渔歌问答。在太湖里行驶的船非常有区域特色,常年在太湖里捕鱼的姑苏大罛船,有七道篷、五道篷,桅杆终年竖立靠风航行。江西山林木材多,驶入太湖的船大多是整棵大树剖开来打造的,内里光洁,外观可见到树节年轮。太湖西岸的船有装丁蜀陶器的缸瓮船,运张渚石灰的竹木船,马山的松枝船、杨梅船,有网船,钩船,对头人船(耥蛳螺船),好夫妻船(撒网船)。我们沙塘港村的船式是“滩船”,一般装八十多担,三丈多长,七尺多宽,二道芦公式篷,不管在太湖中航行或停靠在哪一码头,人家一看就知道它是沙塘港船。
沙塘港村紧靠太湖,农户广种芋头、百合、生姜、萝卜、冬瓜、西瓜等,农作物收获了放家里不值钱,一般都要过太湖运到无锡出售。外头流传这样一句话:港口大老头,当心吃拳头。说的是港口人经常摇船到无锡、常州、苏州去卖菜,码头跑多了,见多识广,与精明的城里人打交道,练就了一张嘴,头老,嘴老。
一群人中间,你很容易看出谁是港口人,一是黑,二是口音硬。这地方紧靠太湖,农人风吹日晒,肤色是黑中带红亮的酱瓣色。他们出门习惯戴顶草帽,礼帽式样。
村里的男人过去都会驾船,会凫水,就连有些女子水性也很好,会走水送饭。爹娘一早摇船到圩田里干活,中午没空回来吃饭,女儿将饭菜装竹篮里,两手举起饭篮,手和上半身不动,两只脚走水,很快就走到对岸,饭菜滴水没进。在太湖边不会凫水,村人取笑为“石秤砣”,不会弄船摇船,那在大集体生产队干活就不能算正劳动力,工分都要打折。
太湖航船,顺风比较容易行驶,速度由风力及篷的高低决定,左右方向由舵决定。偏前方的风就比较难航了。但最难的是横向来的风和顶头风,船只能走“之”字形才能达到目标。假如后两种风能顺利操作,那就是合格的舵手了。
在太湖边生活的男儿大多十几岁就随大人上船,要熟悉船上生活。因为在船上风雨不期,不到边岸晚上都要航行,所以船上的各种工具不管白天黑夜都要能立即找得着,用得准,不得有误,若有失误就有不可想象的事情发生。
出太湖的人碰到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有人摸不到港口,在太湖里急得团团转。这时家里的亲人高高地放起鹞子,挂上鹞灯,系上鹞笛,使湖中船上的人能够看得见听得到,朝此方向找寻回家的路。
船只经常受风浪的颠簸,难免有失风翻船的时候,谁也没有回天之力,只能把平安归来寄托在菩萨身上了。莫看风口浪尖讨生活的人,平日里不论男女,个个骁勇爽利,但是在大自然面前,还是极知敬畏的。村里人驾船出门到无锡一般三到四天归来,若第五天不见归,家中亲人就要坐自家后门口的河埠上守望了,若再不归来,百般无奈,只能求神仙保佑了。因此前辈们恪守太湖船民的风俗,出远门之时都要请“顺风”,用猪头三牲祭请湖神黄泥相公,才能出发。每到大年夜家中请了“利市”,再到船上去请“顺风”,整个仪式有种敬天地、感恩生命的庄重感。有船的人家,孩子吃鱼,母亲会说吃了鱼头能撑篙,吃了尾巴能摇船,希望孩子长大了能弄船。
老胡说,扯篷船在上世纪80年代初被挂桨机船取代,“孤帆远影碧空尽”从此真的尽了。我平时在儿孙们面前讲年轻时在太湖里如何航行篷船,什么风怎样航,儿女们听了似懂非懂,孙儿孙女们根本没见过扯篷船,你讲的他们实在是一懂不懂,但是不管他们要听不要听,我觉得有必要把在我们这一代中消失的扯篷船作为历史回忆一下,因为家乡的扯篷船在我们太湖水网地区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