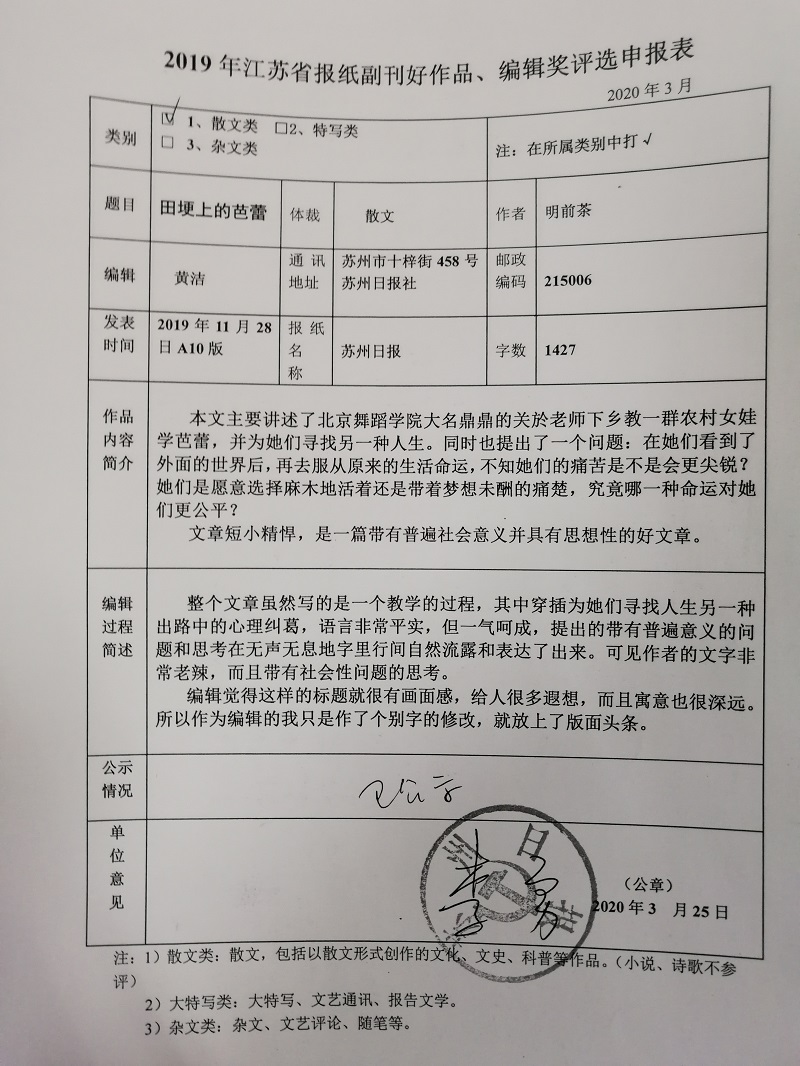
田埂上的芭蕾
明前茶
深秋,我意外遇见北京舞蹈学院大名鼎鼎的关於老师,竟是在河北保定端村的田埂上。村口的原野上,玉米和大豆已经收尽,小块小块的芝麻地上,收割芝麻留下的短短茎秆被太阳晒蔫后,被家长们自发地翻过地,与黑褐色的土地融为一体,给泥土带来不一样的脚感。穿粉色芭蕾裙、白色长袜的当地农家女孩,四人一组,轮流在平整过的芝麻地上跳《天鹅湖》。她们昂首,展臂,踮足,旋转,模拟出天鹅翅翼下的万千情绪。她们用自己稚嫩的身体,去演绎憧憬与绝望,怜悯与忧伤。她们看上去并不像城里的芭蕾女孩一样清瘦又遗世独立,这里的女孩子从小带弟妹、干农活长
大的,皮肤较黑,脸较圆,小腿上的肌肉结结实实,然而,通过关老师的言传身教,她们依旧有了不符合年龄的早熟眼神,浸润在天鹅悲剧中的眼神。
这是她们在国家大剧院演出之后的又一场汇报演出,而围绕在周围的观众,是她们的父母、爷爷奶奶和叔叔婶子们。
这是一拨原先永不会走进芭蕾殿堂的孩子。在关老师到来之前,作为农家女孩,她们通常的命运,是在家里上到初中毕业,出门打工三四年,或者留在家里替人加工枕头套与椅子垫,等待出嫁,等待复刻与母亲一模一样的命运。这里的母亲,普遍养两三个孩子,在繁忙的家务之余,用缝纫机扎100个枕头套,才挣45块钱。母亲们把仅有的资源,都用在儿子身上,她们的口头禅是:女儿都是要出嫁的,培养得再好,有什么用?
4年多前,关於来这里做芭蕾舞培养试点的时候,遇到的阻力是前所未有的。家长们认为,还不如教女孩子绣个枕头套更实惠。关於想了一招让大家服气:“绣个枕套能嫁到疼她的好人家吗?为什么学芭蕾?为了让你们的女儿变漂亮啊!变漂亮才能嫁得好。”
一面教芭蕾,关老师一面像个保姆一样,亲手帮小女孩们洗头、盘头,从北京带护肤品给她们用,免得她们的脸蛋儿一冬一春都是皲裂的。他教她们行走、立脚尖的姿态,教她们以各种方式拉直腿型。鉴于自己是男老师,小女孩的悄悄话不方便告诉,关老师开车去端村的时候,就让妻子张萍同行。
芭蕾,为这些田埂上疯玩的野丫头们撞开了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门。它让她们足尖疼痛,而内心清明;它让她们原本贫瘠龟裂的心田,开出鲜嫩水灵的花来。
小女孩们咬紧牙关用功,无论是技术还是情感,都远远不是关老师初来时,那些眼神木讷、头发凌乱的小丫头了。
最早跟从关老师学艺的小女孩已经快15岁了,马上将走到农村女孩命运的岔道口。要不要带她们去考艺术院校?关老师与张萍爆发了结婚以来最大的争执。关於心软,觉得如果走上艺考之路,孩子将面临残酷淘汰,而农村女孩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自尊心,会受到挫磨。他舍不得孩子遭受痛苦与失败。张萍则以一名母亲的视角看待这一切:难道她们沿着既有的道路走下去,就不会遭受痛苦了吗?按照你的设想,她们就是一名业余爱好者,将来在收获后的田野上,在打芝麻、收玉米的间隙,在田埂上自由自在地跳上那么一段,让沉重的生活暂时退去十分钟,你以为她们就没有痛苦?既然,你已经把她们从混沌麻木的状态中引导出来,她们已经看到了外面的世界,看到了她们本不敢设想的未来,这会儿,再让她们去服从一辈子在农村种地、养娃、扎枕头套的命运,你怎么知道她们的痛苦不会更尖锐?
作为一名底层女孩,她们有着稚嫩的过去,也有着可能极为粗粝的未来。她们是愿意选择麻木苟且地活着,带着井底之蛙的满足感,还是带着梦想未酬的痛楚?究竟哪一种命运对她们更公平?关老师思索良久。
第二天一早,他就带着6位弟子,走上了考学之路。那时端村尚未醒来,草尖上凛冽的寒霜,在朝阳下折射出七彩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