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矩敏
以前揶揄好表现自己的人是“出风头”。我突发奇想,“出风头”是否也可以指很潮的发型?比如鸡冠头、钉子头、朋克头、蝴蝶分、寸头分、渐变纹、短碎发、长侧分,等等。
发型是时代的身份证。以前的先生们多见平寸头、双分或者三七分。资本家是大背头、油包头。军阀是小平头。平民百姓是“马桶盖”、侧分头、光头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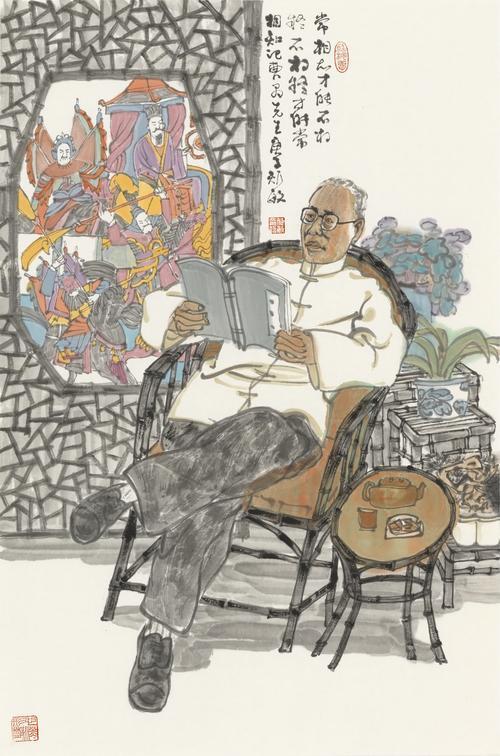
我小时候每次看见父亲从理发店回来,总觉得父亲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鬓角剃得很干净,抹了凡士林的头发簇新发亮。至于童年的我,家里为了省钱,剪头的事都是母亲代劳。她用一把剪刀加把梳子,从两边往中间推,有时候手一抖剪出一道疙瘩,她会沾点水把上面的头发往下梳遮挡一下,然后拿个镜子让我看,证明没有明显的瑕疵。
从初始的马桶盖头到后来的双分头,我母亲的手艺有了长足的进步。再后来,进入青春期的我,开始在乎同学们的品头论足了,于是拿自己攒下的钱到理发店剃头。

当时的理发店会准备几份报纸杂志给等候的顾客解闷。轮到我,我拿着一本《电影》杂志,指着封面上演员孙道临的头像,要求师傅按照此发型剪。师傅噗嗤一声笑了:“你这个小赤佬,头上毛还没长几根,就知道臭美了!”结果还是按老套路剪了个分头。
跨出理发店时,我的头发丝路清晰耐看,师傅用喷壶喷一点水再用梳子搞出个双分头造型,镜子里的我确实蛮精神。一路小心翼翼慢走,拿一份报纸背着风向护着新剃头,生怕风吹乱了发型。路过商场的橱窗,还不忘对着玻璃瞅一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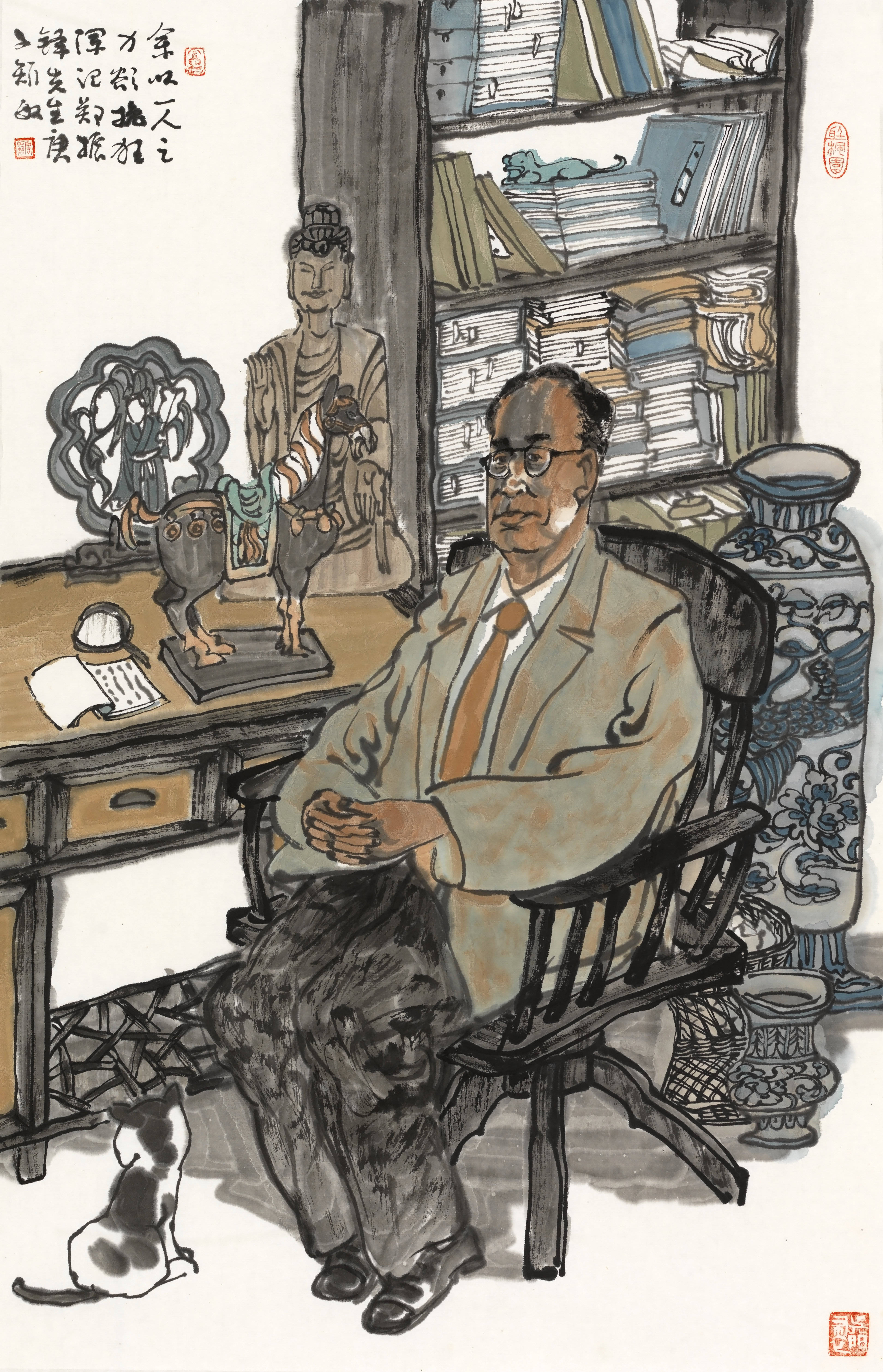
大人头发不乱,是因为涂抹了凡士林再用电吹风做了造型处理。小孩仅是洗发剪发,所以头发总是塌下来紧贴头皮。有次我去理发,趁理发师不注意偷偷用手指抠挖少许凡士林藏在火柴盒内,抹在发际线上。遇风,头发乱舞,唯独那一小撮头发贴着头皮纹丝不动,煞是滑稽。
少年也有掉发的烦恼。我曾写信给北京白求恩医院皮肤科,写得真真切切带着乞求的语气,还把几根掉下来的头发夹在信纸里面,换来医院一句回复:脂溢性皮炎就近治疗。后来有熟人介绍,去看一个老中医,抓了三个疗程草药,服下后腹泻了整整三天。复诊曰:脂溢性皮炎就是要把肚里的油腻泻出来,扶正祛邪;再用生姜熬汤洗头,活血去脂。遵医嘱,结果是邪压了正,头皮被姜水刺激得红肿,还得了急性肠胃炎。
我外公是秃顶,因此我理论上是秃顶基因,没救的那种人。只能平时注意生活习惯,勤洗头、饮食清淡、心情舒畅等,尽量延缓秃发速度。释然以后,我的注意力不再盯着头顶上那几撮毛发,发型也就不讲究了。大学期间都是让同学帮着理发,工作后也是随便找个小理发店将就,这个习惯一直延续至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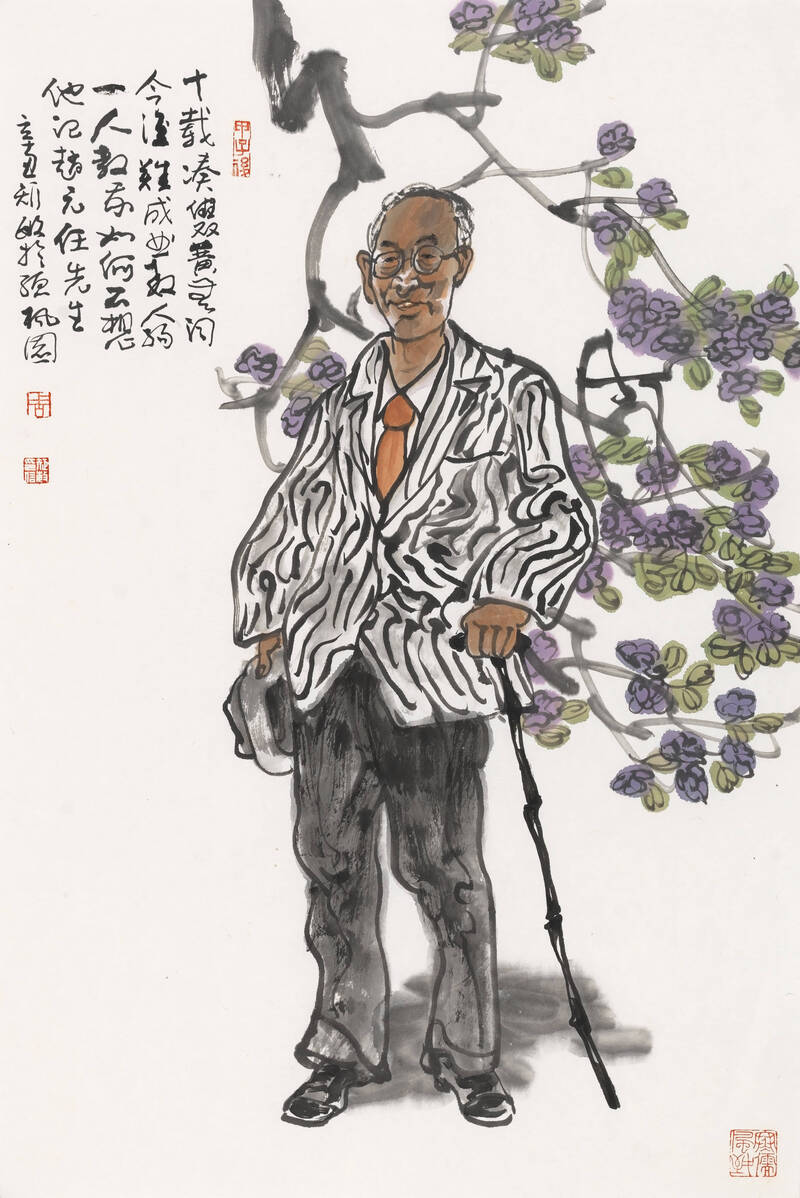
到了知天命的年纪,周边谢顶的男性朋友越来越多。我曾执教的学院有位老教师,时不时用侧面的一缕头发硬往头顶上拽,企图遮盖住寸草不生的荒芜之地。他上课时典型的动作就是不停整理掉下来的那一撮毛。学生们看着窃窃偷笑。其实别人并不在意他的头发,他却很在意。有一次他愤愤然指斥他们小区的理发店手艺太差,原来理发师把他那无比珍贵的一撮头发给误剪掉了,他不停投诉,讨要个说法。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过我始终搞不懂,仅剩一撮毛了,还去理发店干嘛?
与这位老师相比,我的状况还说得过去。头发虽不茂密也不算寒碜,有点小得意。我的职业和秉性决定我只能选大众化、稳重点的发型,决不能搞标新立异。
也有例外。一次临近春节前,我路过一个高档的美容美发店,正值开张之际,全场八折优惠,于是就走了进去。店长很热情,使劲夸我皮肤白、形象好,必须设计一款能充分体现我气质的发型,并自我介绍他是从日本学艺归来等等。于是我带着十分信任的态度坐下来任其摆弄,又是染发又是烫发,忙了整整一个多小时后,出现在镜子里面的是:一头棕黄色略带卷曲的发型,如果再配上一件花衬衫,就是一位“潮哥”的形象。店长和店员啧啧称赞:洋气!我一贯中庸,还没胆量如此前卫。加钱!再复染成黑发。之后我再也没踏进过大的美容美发店。
我小区隔街有家理发店,店主是一对从苏北来的年轻夫妻。小巷理发店要吸引回头客,口碑、手艺、性价比、服务态度都是顶顶要紧的。小老板主持,老婆辅助有条不紊,每逢节假日顾客盈门,还需提前预约。依稀记得他有两个小孩,女孩先天痴呆,待在家里,偶尔坐在店里楼梯上玩手机。她是姐姐,弟弟上初中,学习挺优秀。
最近我又去理发,理发店已经人去楼空,门口贴了一张条子,“家中有事不能营业,买了本店VIP卡的可以办理退款,留下了联系电话”。听隔壁邻居说,小老板骑电瓶车没戴头盔,和收废品的三轮车相撞,车上翘着钢筋……他猝然离世。我默默地在店门口站了许久,转身把存有余款的卡随手扔进了垃圾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