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尔
《夜航船》是眀末清初文学家张岱所著的一部百科类图书。其实,在集体劳动的年代,夜航船是家常便饭,我们称为开夜船。夜航船与开夜船同一意思,前者是艺术化的用语,后者则是我们乡下人的语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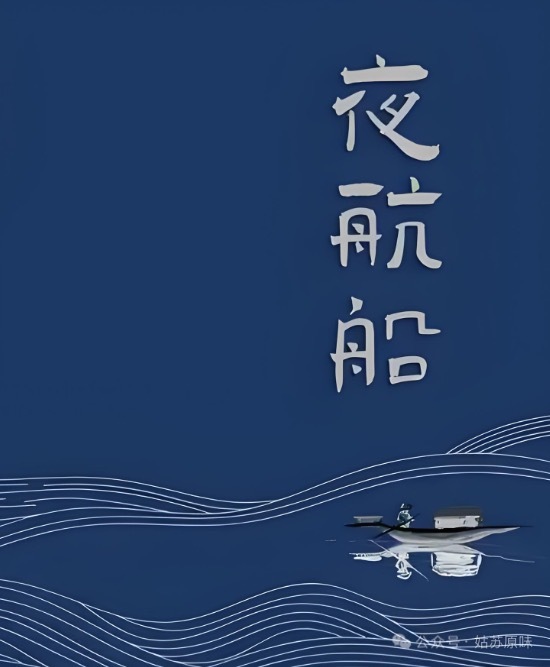
“插队,二点钟了,动手啦!”社员金桃在敲我的玻璃窗。我正睡得香,猛地惊醒。披上衣服,拿好之前准备好的饭菜,立马跟他往河边走去。他带我去杨林塘罱泥。队里一年四季都在想方设法把河底那层宝贝疙瘩弄上来——早春一过就开始割草积肥罱河泥了。从队里出发经盐铁塘再拐入杨林塘有四五里水路,我俩轮流摇船。那条四吨的水泥船在黑漆漆的夜色中缓缓前行。
月亮钻进了云层里,没有照明工具,仅靠水面的波光才能辨明哪是河、哪是岸。第一次摇夜航船,我一直担心“吃草”。所谓吃草,就是船头撞上长满野草的岸。金桃告诉我,不要怕,看准前面发亮的中心地带摇。早春的夜寒气足。料峭的冷风中吹来田野芬芳馥郁的气息,水面上缕缕薄雾向我们扑来。河岸两边种着蚕豆,尺把高的豆萁整齐划一,似列队的士兵,河岸边一幢幢简陋的农舍影影绰绰。忽然想起了中学里学过的《社戏》。迅哥儿和他的小伙伴摇着船去看戏,不也是在两旁长着蚕豆和麦苗的河流中穿行吗?

行了近两个小时船到杨林塘,借着破晓前的光亮,金挑开始动手罱泥。他发力用竹竿插入河底时,我就使出吃奶力气拼命摇船不让船倒退,待到罱网起水时,才能松口气。
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积肥是生产队一年四季都要干的活儿。队里一条八吨木船,每班四人轮流开上海装黑粪。来回约一周。那次队长安排我开上海。一行四人起锚出发。队里那条船称使篷船。它有桅杆有篷,顺风时扯篷。风来了,白色的篷布如升旗般冉冉上升。一阵大风刮过,我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力量——风帆鼓了起来,一条八吨的空船登时像装了马达,船头雪浪翻滚,耳闻浪花拍打,一副大江东去气魄。可是,大部分的行程还得靠摇船。四个男人轮流不停地摇。到了夜里,啪啪的水声中,夜航船摇橹前行。那年头的河道比较窄,南来北往的船又多,为防止相撞,每条夜航船上挂一盏桅灯在船棚右边。我们做着机械的摇船动作,手臂越来越酸,眼睛越来越涩,另一组的俩人把我们换下。摇呀摇,摇呀摇,也不知行了多少路。船老大说,明天又是个大太阳天,夜里风凉要多摇摇。手臂酸得举不起来,我半躺在船舱里等待着替换“上岗”。我说:“吃不消了,一直这么摇,要摇到几时?”船老大说:“你第一次开上海不知道,夜里船不能要歇就歇,要找个桥洞或大树下才能安全过夜,天热就是靠搖夜船前行的。”我睁大眼睛寻找桥,发现前面有座黑漆漆的大桥,心中不由暗喜。可桥洞两边已经有船停泊了。环顾前后,水面上星星点点的桅灯越来越少了。可我们还没找到归宿地,于是只好不停地摇。“依一一呀,依一一呀”欸乃声在静夜里特别刺耳。船老大在橹槽里加了些菜油,声音变得柔和些。终于,前面有座桥,桥下没有泊船。船老大说,好!今晚就在这里歇夜吧。
第二天船过黄浦江,在上海军工路码头装上黑粪后开始返航。为了早一点回家,我们白天拉纤晚上摇船。可是这与来时不同了,夜航船吃水深只能慢吞吞向前滑行。空船时我们走绷摇,所谓走绷就是两个人同时向前走一步,把橹推出去;紧接着同时后退一步把橹拉回来,这样人省力船速也快。但是前舱与后舱都装满了黑粪,脚不能来回走动,为提高船的稳定性,只能用腰部力量靠双手推拉,让船平稳前行。夜航船似一头负重的老牛慢悠悠前行。夜风里带着阵阵臭味,呛得人头晕眼花。所谓黑粪就是阴沟水,那个年代缺少化肥,大上海的阴沟水都是我们乡下农民的宝贝。开始一段时间我很不习惯,说也奇怪,一天到晚都是这个味,慢慢、也习惯了。船上活力气用得大,饿了也不管臭不臭了,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一周后,承载着一船的农家宝,同时也承载了我青春的快乐与艰辛,船又回到那个熟悉的岸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