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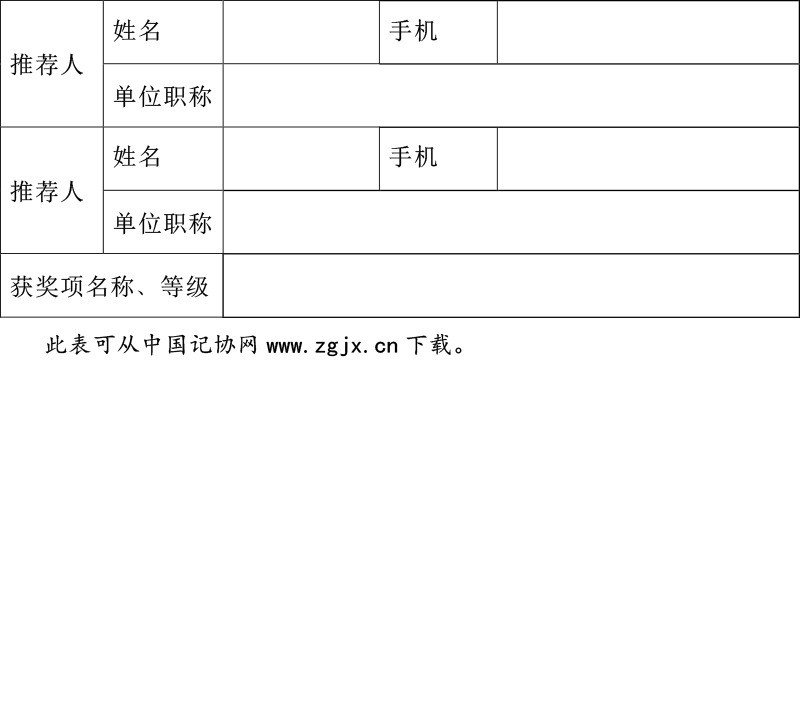
走进安宁病房,触碰人们最深的痛与爱
直面“终点”——是告别,也是新生
□ 本报记者 冯圆芳 杨昉 姚依依 策划 杭春燕
在解放军东部战区空军医院住院部十楼,设有疼痛医学科(安宁疗护病区)。一扇大门,隔开了两个世界,一边是喧嚣熙攘的烟火人生,一边是弥留者缠绵病榻。逝者如何善终?生者如何作别?门里门外的故事,关乎人最深的痛与爱。
面对病痛的“宣战”与“和解”
东部战区空军医院的安宁病房,几乎全部位于这栋楼向阳的一侧。在一间名为“环游”的病房里,76岁的退休翻译、如今已满头白发的南京大学“新三届”学生孙中文,微蹙着眉头,努力和记者打了招呼。儿子林海温柔地伏在她床边,不时喃喃细语。
2020年11月27日,林海的父亲就是在这里走完了生命最后一程。至今,林海仍觉得那是命运的玩笑:“父亲50年来风雨无阻地锻炼身体,退休后仍每天坚持跑5公里,但疾病绕过内脏四肢找到大脑——他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和帕金森病。后来,他一天中似乎只有两三次能认出我来。”
林海一向乐观自律,总觉得自己可以做很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当父亲即将面对死亡时,他的第一个念头是:“不能惜财。”盘算完财产后,他发现自己可以拿出150万元作为对抗命运的“底牌”。
林海想送父亲去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医院治疗,甚至希望采取朝脑部植入电极的方式以改变状态,但医生看完检查报告后否决了可行性;他在南京几乎跑遍各大医院,但医院不愿长期接收毫无救治希望的病人;退而求其次,他发誓要尽可能让父母住进最好的养老院,但随着父亲的并发症越来越严重,养老院表示无能力护理照料。万般无奈之际,林海偶然了解到东部战区空军医院可提供安宁疗护服务,便朝着心中这一丝光亮奔走。
安宁病房什么样?在林海原先的想象中,这里是“送人走的地方”,或许是灰暗的。来到病房的那天,他惊讶地发现,这里有阳光、音乐、芳香,有休闲吧、植物角、谈心室,连病人仰卧病床时面对着的天花板,都被贴心喷绘上旖旎风光。区别于普通病房,安宁病房关注的重点是控制疼痛等不适症状,而不是阻止原发疾病的进展,医生的角色也更像心理治疗师。疼痛医学科主任周宁和林海的一番谈话,让他高度紧绷的身心松弛了下来——
“如果你父亲的病仍然有治愈的希望,那么你应该全力以赴。但如果没有,你的努力会不会徒增他的痛苦?”
“你的父亲也许明天就不在了,但今天他还在。你今天走进病房看到父亲还在,你开不开心?”
“你不要想更多和明天相关的事情,先把今天过好。”
“他已经没法做决定了,你必须为他做出一个负责任的决定:他想要什么?什么才是真正为他好?”
“听完周主任的话,我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林海感到自己的生命观被彻底颠覆了,“许多医生都有可贵的职业精神,治疗过程让我和父亲的生命纠缠得更紧密——这当然是善意的,但周主任的话让我以更宏观的视角来看待这一切,把我从‘泥潭’中往外拉。父亲患上阿尔茨海默症,这是种至今连发病机制都没完全搞清楚的疾病,怎么可能靠我一己之力逆天改命?”林海开始想:或许应该更多站在父亲的角度来思考,他虽然不能说话,但他的眼神分明在说,“我只想睡个好觉,我希望获得身体的舒缓,我希望余下的日子能够愉悦。”
自从服用巴氯芬、丙戊酸钠控制癫痫和解除抽搐后,父亲的状态逐渐平稳下来。最后的日子里,他有时大概认出了心爱的独生子,使劲冲他眨巴眼睛,眼神安详愉悦。这些温馨的细节照亮了林海在父亲去世后的漫漫长夜——死亡似乎也不再狰狞可怕了。
父亲去世后,林海带母亲去仙林泰康鼓楼医院看骨折。拍完CT,医生悄悄往他手里塞了张纸条,上面写着两个字“转移”。之前发生的骨折,实际上是乳腺癌骨转移所造成的骨质脆化。
“孙中文,你知道吗?当年咱们一起在大沙河插队时,我的腿被拖拉机轧了,你背着我拼命地往镇卫生所跑。那是我这一辈子觉得最安全的时候……”病床前,林海举着手机,给母亲看她同学发来的视频。阳光和煦,母亲婴儿般蜷卧着,在氟比洛芬凝胶贴膏和洛芬待因缓释片作用下,她身体感到舒缓,渐渐陷入对往昔的追忆中。
历史长河中,每个人的生命不过沧海一粟;对于个体而言,所亲所爱是最绵密的羁绊,在宏观与微观的视角间,很多人在艰难地挣扎,又努力着超越。父母生病以来这些年的切身体验,让林海更加领悟“活在当下”的意义。现在每次探视结束与母亲告别时,林海总会说“See you tomorrow”。
明天见!他尽力不去想更久远的日子——母亲今天还在,明天也在,那么,眼下就是最美好的时刻。
传统观念VS“我”的心愿
陈晨永远忘不了那一幕。2020年6月14日清晨,在家中长辈的坚持下,即将咽气的母亲被送上救护车,从东部战区空军医院安宁病房转运至家中。搬抬担架之际,母亲突然出现了濒死症状:面部扭曲,两眼上翻,“啊啊”地大声喊叫,嘴里满是鲜血。这,成为陈晨久久挥之不去的梦魇。
6月初,罹患晚期宫颈癌的母亲刚搬入安宁病房之际,周宁就曾郑重询问陈晨:你有没有想过最后你母亲在哪里“走”?陈晨愣了一下。而周宁清楚其中的区别,以往病例中,曾有一对获得拆迁房的夫妇在幼子咽气前坚持把他抱回家,为的是让孩子看看家里的新房;一位浦口的高奶奶,带着镇痛泵回家,最后在儿孙陪伴下安详离世。对中国人来说,生老病死不仅是自然规律,更被赋予了文化习俗的浓厚意味。
陈晨回到病房询问母亲的意愿,母亲的答复斩钉截铁:坚决不回家,死也要死在医院里!陈晨明白,她是不想再回到那个伤心地了。
“你这病,到最后就是疼死的。”和母亲争吵了一辈子的父亲,有次在她床边冷冷撂下一句话。没有鼓励与支持,甚至露面也不多,让母亲彻底寒了心。
陈晨的姨妈和舅舅坚决不同意让母亲在医院里“走”,对着陈晨大声说道:“你年纪小根本就不懂!她必须回家,不然灵魂永远在外面流浪,永远找不到家门!”
强大的习俗铸成一道铜墙铁壁,在它面前,病人自己的意愿似乎不值一提。学音乐的陈晨有一颗敏感的心灵,她痛苦、无奈,夜不能寐。前两年她带着母亲四处求医,可谁知母亲临死也难得安宁。她无数次替母亲不平:为何在病床上仍然得不到体谅?为什么习俗比母亲最后的心愿还重要?
人是生活在文化之中的,习俗也有它存在的道理——周宁宽慰她。
时过境迁,如今陈晨开始有些理解长辈们的选择。她想起当时舅舅在她身旁坐下来,双手抱头,一言不发,十分痛苦纠结。她又想:如果母亲最后真的在医院咽气,那种孤零零的滋味,她怕是也不会喜欢吧。
周宁劝陈晨把母亲去世前后的这段经历写下来——对家属的哀伤辅导,也是安宁疗护的一部分。陈晨哭得不能自抑,眼泪一滴滴落在电脑键盘上。
她的文字不止于叙述一己遭遇,事实上也在追问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命题:中国人的生死观念、文化习俗能否随着社会发展一同演进?为什么普通医院的许多医生对患者及其家属的遭遇还难以做到感同身受?除了安宁疗护阶段,如何给予患者更多人文关怀?这一服务能否更普遍地开展?
不再怨恨,让彼此少一点遗憾
“请问是丹丹吗?我是东部战区空军医院疼痛科周宁。你父亲走之前想见你一面,你愿意来吗?”
打这通电话,周宁称自己是“多管闲事”。此时翁先生罹患的结肠癌已经发生肺转移,生命进入倒计时,唯一心愿是见见亏欠了一辈子的女儿。约30年前,他和妻子离婚,之后没再付女儿的抚养费。孩子的伯伯、姑姑既想帮他圆这个心愿,又怕遭骂,掂量半天后说:“还是算了吧。”周宁想,如果能让父女俩见面,是否会让双方都减少一点遗憾?
父亲是谁?电话那头的丹丹费力地回忆:父亲是她上小学时偷偷找来,眼神陌生又有一丝温柔,和自己说他是爸爸的那个男人;也是自己面对作文题目《我的爸爸》根本没法提笔去写的那个人。“在此之前和他走了之后,你都可以理直气壮地恨他。但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能否为自己的人生预留一点余地?”周宁试着劝导。
第一次见,场面平淡。他们呆在一起的几分钟里,虚弱的父亲只是看着她,不语。唯一发生的事情是当他咳嗽时,丹丹下意识地俯身帮他擦了痰。他看着她,有些惊讶,但依然没有说什么。
周宁与患者家属保持联络,进行不定期回访。今年清明前,丹丹和爱人与周宁相约。丹丹说起一直盘桓在自己脑海里却始终没说出来的疑惑:父亲是否爱她?
“在周医生联系我之前,我爸爸也曾经找过我,只说了一句他生病了,什么病、严不严重,都没说。他一辈子都是这样。加了微信之后,有时我主动讲起自己的事,很难过地跟他说:如果这么多年来有你一直陪伴着我,我的人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我也不会走了那么多弯路……但他就是不回复我。”丹丹几近嚎啕。最深的怨念、最大的缺憾和最渴盼的爱,都埋藏在这短短几句话里。
周宁对丹丹说:“你是一个善良宽容、敢爱敢做的人。给你打电话时,我就相信你会来。你只要想通了,就会一直朝前走。”
而如果时光可以倒流,如果面对所爱之人能够摆脱缄默、勇于承担责任,是否人生会少很多遗憾?面对死亡也多一份坦然?
爸爸!在父亲病床前,丹丹终于喊出了那个在心中喊了无数遍的称呼。父亲当时一怔。2017年2月,父亲去世后,周医生说服丹丹以女儿身份出面料理丧事,光洁如镜的墓碑上,写着“爱女丹丹 立”字样。
接二连三处理了父亲、外婆、公公的丧事后,丹丹也更深切领悟到,爱与陪伴是支撑人走过最后一程的动力,这决定了生命如何画下句点。对人们来说,重要的是如何对待当下、珍视生者。
东部战区空军医院安宁病房里,包括林海、陈晨、丹丹在内,很多人的命运曾先后交汇于此,又很快辐散开来。他们并未因为亲人的离去变得消极,而是更慷慨更善意,更愿意悦纳自我,让生命焕发出崭新的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