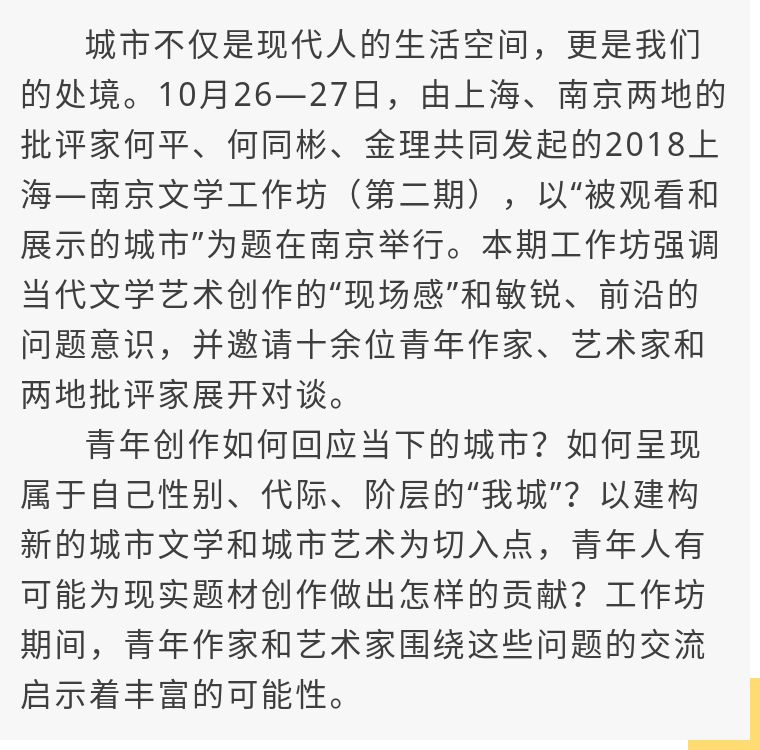


随着科技在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我国的科幻文学也从原先的边缘位置逐渐走向中心。我认为科幻小说同样是现实主义,在科幻的外衣下提供了作家对于社会的想象和理解。就我个人创作而言,我的作品通常以城市为背景,探讨城市人与科技的关系。我的一部长篇小说《荒潮》以电子垃圾回收中心为原型,写工人们从电子垃圾中,提取出一些稀有金属或者有价值的东西进行回收。这个过程中的生态问题、人际冲突,都构成了我的“科幻现实主义”。
有没有可能以技术视角来观照我们的现实?郝景芳的《北京折叠》就在探讨怎么从机器、算法、AI的角度重新发现我们身处其中的城市。我在小说里也写到,一位主角和机器发生了结合,带领他的伙伴们入侵城市网络,以机器而非人的视角去观看整个城市,我想这种视角也许能为我们理解今天的现实提供一个新的维度。


其实当代文学对城市的书写是很不够的,至少我想不起来有哪一部作品很好地诠释了作家眼中的城市精神,写出他们自己对城市的理解。就我个人来说,我对现代城市的一个主要的看法是它许诺给现代人的“自由的孤独”——个体的孤独是大城市生活的常态,从另一方面看也是对个体的馈赠,因为他们可以重新选择、建构自己的社会关系。在我写小说特别是写到北京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这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来历,但在这个城市里,他们的来历恰恰不必被讨论,城市赋予了他们“匿名”的自由,这就是我眼中非常重要的城市精神。我们总说“月是故乡明”但生活里不能总看月亮,还是要回到我们生活的现实中来。


我近两年写的短篇小说基本上都是关于从2000年到2010年差不多十年之间的大城市生活。我16岁之前住过的所有房子都被拆除了,2002年我考入复旦大学,大学校门外,宿舍区,父母家门口,以及自己租住的房子周围,所有的地方都在挖掘,推倒,建造。这就是当时我身处的城市和现实,为了最大限度地接近这个正在飞速改变的城市的深处,我常常骑车在城市中穿梭。在我的处女作小说中,建构了一座“桃城”,我把自身对于城市化进程的思索融进了小说创作中。
有意思的是,我发现我对这段时期的上海的书写,和金宇澄的《繁花》非常不一样。用评论家张定浩的话来说,我们都呈现出了只有我们自己的维度才能够看到的世界。在对现实进行书写时,作家应避免和警惕的恰恰是视角的单一性。敏感和敏锐理应成为作家的精神特质,当自己身处的这片世界突然发生了松动,有了不对劲的感觉,作家应当在第一时间捕捉到。


我最近的小说关注手机和现代人的关系,这个已经构成了现实生活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马歇尔麦克卢汉认为,媒介是人的感觉能力的延伸,所以手机其实就是人的身体的延伸,人的情感和家庭关系的延伸。譬如异地恋,恋人们需要依靠这部机器(手机)来维持恋爱的体征。不光是爱情,亲情也是这样。很多从福建来打工的移民,他们没有大多数中国人重视团圆的概念,他们家庭的团圆常常是在机器中实现的,就是和家人通视频。我在小说里写到一个情节,一个小孩在2001出生,直到2007年,他都处于事实上的“孤儿”状态,直到2007年,他的妈妈“从手机里”回来了,他发现妈妈长得和手机里一个样。所以手机和互联网营造的虚拟空间也是现实的一部分,这算是我切入现实的一个维度吧。


我是做小剧场话剧的,想谈谈小剧场话剧和当代城市之间的关系。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中国的小剧场话剧已经形成了反商业、重思索的鲜明特质。小剧场更关注青年性,“青年性”和“青年”在我看来是不同的。中年甚至老年的创作者一样可以具有青年性,而现在很多年轻人却失掉了青年性。什么是青年性?我认为可能是和庸俗或者媚俗的东西做对抗,对当下的一些迫切议题做出回应。德国的剧场就非常关注难民等社会议题,当然也还有很多中产阶级习惯看歌剧,关心“你为什么还不结婚生孩子”的问题。所以现在做话剧常要面临的是如何争夺年轻人的注意力,如何在商业化潮流中生存下来。
我写剧本主要关注两类城市人,一种是偏离正常生活轨道的人,一种是生活在城市夹缝的人。一些城市人并不愿按照社会习俗设定的轨道去生活,这些背离轨道的人可能更隐喻着生活的日常。还有生活在城市夹缝中的人。我最近写了一个剧本《在荒野》,剧本的灵感来自2013年的一条新闻《回不去家的人》,一个记者在北京西站看到很多人生活在那里,他们出于各自的原因来到城市,却无法融入城市,甚至走不出第一站,但也没有办法回到家。这里面有很多触动我的东西。现在我们会特别想要去开掘一些新的城市空间,寻找新的议题和新的人物。


我对城市的关注可能超过了对文学的关注本身,或者说文学是我关注城市的行动方式。我平常挺爱瞎走瞎看的,写作时不大书写私人经验,而是更关注公共经验,例如老旧街区中城市平民的生活现状,我自己也生活在这样一个空间中,喜欢观察熟人社会里普通人的生活细节、人际关系、人情人性等。有人说,我小说的价值在于题材方面的“下降”,沉入市井生活中,还有网友说,我的故事让他们在经过老小区时,愿意停下来看一看,听一听,那是我觉得我的创作最有价值的一刻。
最近关注的是大型活动吉祥物(海宝、福娃等)在城市里的生存现状。吉祥物是官方确立的城市形象符号,但它往往是一次性的,转瞬就被忘记的。我很希望当它们作为符号的使命结束之后,能够被集中地搜集和展示,以吉祥物这样一个小小的切入点,唤起人们对城市历史的记忆。


在当下的现实题材创作中,一个不得不正视的问题是:什么是今天的“新城市”?从“新城市”出发,我们可以建构起怎样的“新文艺”?当有着不同传统和地方经验的中国当代城市进入新的世纪,无论是外在的城市景观和空间结构,还是人和城市的关系、城市里的人际关系,以及人在城市的生存境遇,都在发生着空前的变化。本期工作坊希望以“被观看和展示的城市”为切片,看到新一代中国作家、艺术家有别于传统的差异性,以及他们之间文学艺术创造的差异性。我们这次邀请的作家和艺术家,出生地几乎都是城市,比如笛安的太原,周嘉宁和张怡微的上海,朱婧的扬州,王占黑的嘉兴,黄淞浩的郑州,陈楸帆的汕头,等等。他们从不同的城市走出,又在北京、上海、杭州、南京等地接受大学教育,有的还去到巴黎等国际大都会留学。从这些“新城市”“新人类”中诞生的合乎逻辑的“新文艺”究竟会是什么样子的?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中国当代文学及艺术的新变革理所当然地应该发生在你们中间。
记者 冯圆芳 顾星欣









